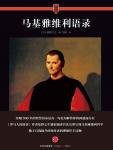《幽巷谋杀案》的笔记——不可思议的窃贼 第8节
2024-04-24 21:52:44 (0回应)基把卡林顿家的莫里斯车停在门前。
祖安翻译,哈哈哈哈....

《七面钟之谜》的笔记——第四章 一封信
2024-04-14 18:40:08 (0回应)老卫德跟她母亲出奔——他老是干那种事。除了已经属于另一个男人的女人,没有一个女人他中意。
曹老板:哇,异国他乡遇知音!

《展望塔上的杀人》的笔记——都市之声 第四节
2024-04-05 11:38:32 (0回应)如果想让一个人走到哪里都能听到打给他的电话,那得是多么大的工程啊!
然而现在不需要什么“大工程”,只需一部手机就能做到

《谁杀死了秦帝国》的笔记——第五章 嬴政暴毙,赵高得势
2024-03-21 10:44:43 (0回应)他还多一个致命的敌对因素,就是人们有着回归分封时代体系的历史惯性
第一次学到历史惯性这个词。

《谁杀死了秦帝国》的笔记——第五章 嬴政暴毙,赵高得势
2024-03-21 10:41:05 (0回应)秦始皇所做的所谓坏事,不过就是在皇权专制开创的道路上,为后代帝王做了扫路的炮灰。
后人会装模作样的肆意评判前人,已彰显自己的正确。

《天国的子弹》的笔记——首都髙速公路的亡灵 第二章
2024-03-16 16:53:10 (0回应)你快想想办法啊,你不是个男人吗?!
遇事就打性别拳,小仙女是这样的

《卖毒的女人》的笔记——土地杀机 第五节
2024-03-13 15:59:43 (0回应)可有时,就会用从国外进口的次品,
某国?????????

《中国历代通俗演义02·后汉演义》的笔记——第九十回 济父恶曹丕篡位 接宗祧蜀汉开基
2024-03-11 17:35:53 (0回应)第九十回 济父恶曹丕篡位 接宗祧蜀汉开基

《卖毒的女人》的笔记——饥饿都市 第一节
2024-03-09 12:49:12 (0回应)她竞然开始低声说:“什么嘛,这是什么店嘛,简直就是无赖。自己店里的厕所锁不上,反倒怪客人,究竟打的什么主意啊?……我吃惊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简直就是无赖!”
可以,这很小仙女。。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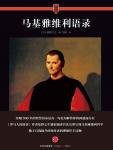
《马基雅维利语录》的笔记——第三部 人间篇 14
2024-02-28 15:15:48 (0回应)第一,只有具备忍耐与宽容,才能够消解人与人之间的敌意。
第二,只有给予对方报酬或援助,才能促进敌对关系的好转。
第一,只有具备忍耐与宽容,才能够消解人与人之间的敌意。
第二,只有给予对方报酬或援助,才能促进敌对关系的好转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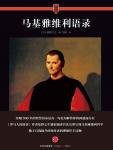
《马基雅维利语录》的笔记——第一部 君主篇 01
2024-02-28 11:47:21 (0回应)一个在任何方面都以善行自持的人,在置身于恶者之中时,难免遭到毁灭的命运。
因此,想要保全自己地位的君主,必须知道怎样成为恶者,并且必须掌握在何种情况下有必要真的做出恶人一般的行为来。
作为一名法官,心持善念,但外要了解恶人是如何形成以及恶人的行为,并如何制恶。

《鼠疫》的笔记——第一部
2024-02-06 09:06:19 (0回应)一半像殡仪馆埋死人的人,
看成殡仪馆里的死人。。。

《纯真博物馆》的笔记——47、父亲的辞世
2024-02-03 13:29:14 (0回应)自私的人,无法对他的痛苦产生同情

《惊奇物语:超好看01》的笔记——传奇篇 旱魃——文/万象峰年
2024-01-15 21:40:52 (0回应)除了12个矿工的家属,其他人都很高兴,载歌载舞,行拳猜码,就差没上文艺队了。在要不要向上级汇报和请求大型水泵的问题上,大家的意见很一致——不要。水象征性地抽了一会儿就停住了,因为蓄水池装满了,抽到池塘里扛不住蒸发和渗透。经过全村的民主表决,一致同意停止抽水,保住这座天然水库,并且大家一致投票同意井下的人已经死了。
陈太明没有表示太多的反抗,因为他已经反抗过了,被老村长指着鼻子骂不识时务,被护矿队从矿上绑回来。
农村,朴实善良,乡里乡亲,呵呵呵

《惊奇物语:超好看01》的笔记——传奇篇 旱魃——文/万象峰年
2024-01-15 21:27:58 (0回应)村委会象征性地成立了水失窃事件调查组,但是他们更多的是幸灾乐祸——如果大家都瞎了,谁能容忍一个明眼人存在呢?
恨有笑无,典型的某锅农村